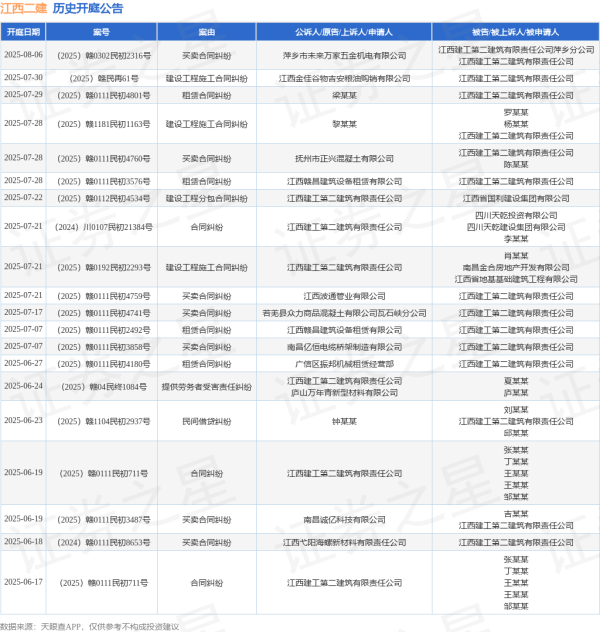阿宽给人的印象是高挑的身材、看起来不很健谈却与人为善的性格炒股配资平台选,再加上不甘于无聊的心气。
曾经空少的身份只是帅气外表的注脚,现在的他已经决心扎根农业,播种可以长得更高的理想。
阿宽的鞋底粘着泥土,脑海里平铺飞行的精密航图。



“不上班”的农人生活
城市人的最大心愿之一,或许就是“不上班”,但“不上班”并不意味着想象中的闲适自由。新农人阿宽“只要从睡觉醒来的那一刻开始,就没停过”。他的工作时间并不规律,而是完全取决于作物的情况、天气的变化,还有各种突然出现的随机任务。最近,他通常七八点起床,有时干到傍晚五六点,有时要忙到深夜12点。“我回到乡村这么久,始终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——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后面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到底会发生什么。”每天都有新情况打破阿宽原本的计划:地里出问题、上级考察、临时采访、工地监工……
在做空少的那些年,他习惯了提前半个月收到排班表,清楚地知道哪天工作、何时空闲;而现在,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”,成为新常态。农业的“自由”,其实等同于随时待命的责任。“就像在自己家一样,你要收拾的话,有无数个东西可以收拾。”从农场建设到内容运营,从种植到接待游客,所有事情都与他有关。
一开始做义工,农场主干什么就跟着干什么;现在自己开了营地,决策上就无法再依赖别人。“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多了,要操心的也就多。”两三年的新农业经历让阿宽发现,乡村创业、就业的人员流动性极高,年轻人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最近00后的种植小伙子走了,他就得亲自上阵。
那个“不想一眼看到头”的
孩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了
阿宽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农民家庭,父母种地的背影是他童年对土地的记忆。小时候跟着他们在田里干活时,小小的男孩蹲在地上,手里攥着杂草,抬眼看不到田地的尽头。因为又无力又无聊,于是闹脾气把爸妈前面刚插的秧苗揪出来,然后就可想而知地被“禁入田地”了。那时的他,完全没想到多年后,自己会重新回到这里。
疫情结束后,阿宽正式辞职。那时他已飞了6年航班,收入稳定、生活体面,但“我不想一辈子只做飞行一件事,不想一眼能看到头”。辞职的那一刻,他清楚收入会断崖式下降:从做空少月入1-2万元,到当农民头2年只赚了1万元,他的坦然态度是因为早有预期:他见过身价千万的投资人也在农业创业中失败,就像任何领域里的创业一样,农业当然也有“重资产、高风险、低回报”的可能。但机会与风险的辩证,阿宽在入行前就想通了,所以收入的改变,并没有打破他从未抱有的幻想。
阿宽最初去临安一个农场当义工,农场主是互联网出身的“农业小白”,两年半亏了200多万。阿宽敢入这一行,并不是因为有家底,而是因为“新农业和传统农业完全不一样”。他在杭州的这段时间,吸收了大量一手信息和经验——从农场经营模式到农文旅业态。在越来越多人选择保守的时代,阿宽的创业逻辑,不是冲动下水,而是长时间观察与尝试后的理性入局。
在他看来,传统农业靠体力,新农业靠技术、信息。父亲一个人现在可以管四五百亩地,机械更新、耕作减负,农业生产已不再只是辛苦。父母对他选择回乡创业持开放态度,“我跟他们说了,在城市背上房贷、车贷生活的话,也就那么回事儿”。经过对比,他发现普通上班族与新农人收入差距并不大,而这条路的天花板,由自己定义。
镜头拍不到的
“悠然见南山”是镜头赋予乡村生活的浪漫幻象,实际上阿宽现在总是“带月荷锄归”。现实的农村条件不如城市完善,配套不足,创业者要自己建立一切。年轻人被城市便利“宠习惯了”,要重新适应乡村的“原始系统”:没有外卖、地铁、电影院、健身房,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。“这里没有城市的娱乐和便利”。那些抱着田园幻想的人往往失望离开。
生活条件对比最直观的一方面,隐性的参差其实更难提前预料。“我觉得乡村生活其实挺难的,很多人一来就想创业,但这里没有标准流程。”加上农业生产的复杂度、人员的不稳定、信息不对称,让新农人时常陷入高强度的精神内耗。如果抛下一切孤注一掷,精神压力不用说肯定爆表。
除了个人层面“没有标准可参考”,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氛围也差异明显。杭州之所以能吸引阿宽,是因为这里信息密度高、新政策多、离市场近、资源集中,这些条件能促进新农业更快落地。阿宽并不是“逃离城市”而被迫创业,他看中了土地蕴藏的试验空间。
他也给后来者提了醒:新入行者最好“要么有人带,要么家里本身就干农业”。“千万不要两眼一热就自己去包地种地。”在他看来,农业创业要因地制宜,遵循地方气候、产业与消费结构。“自己之所以能做“农文旅”方向,是因为杭州的城市性格、交通条件、消费偏好都合适。”
这几年阿宽没少因为突发状况“崩溃”,但也在一次次感受着“一切都值得”。第一年,他每天干活、偶尔拍视频,不知道意义何在;第二年,自媒体突然被关注,上了综艺《种地吧少年》,那是一个转折点。后来他带着五六个年轻人一起开咖啡馆,大家从零开始搭建农场,“开业那天,二三十个朋友围着我,我发表了感慨——一下子就性情了。”虽然团队后来解散,但这些瞬间让他确定:选择是对的。
新农业复合系统
阿宽现在的项目叫“令人向往的农场”。它不只是一个城市周边的采摘农场,更像一个集中多重体验的复合系统。营地的主要客源来自抖音和小红书,客人要么是奔着采摘来的,要么是想感受“美好的乡村生活”。营地有大棚种植奶油黄瓜、番茄、草莓、蓝莓,主打四季采摘,衔接咖啡馆、轻食与露营活动。企业团建、政府活动、生日宴、露营聚会——有更多人看到并认可了乡村生活的“好玩”之处。
在阿宽看来,这种“农文旅”模式,本质上是城市逻辑与农业逻辑的结合。农场吸引客流,客流带动消费,咖啡馆和轻食满足需求,活动反哺品牌。“但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核心的农业。”在“农文旅模式”之外,科技与政策也在重塑农业体系。虽然农业自动化程度提高,但真正高效的设备成本也高,创业初期仍要靠人力填补。“技术和器械的意义,一方面是节省人力,一方面是让农业标准化。”智慧大棚、植物工厂、控温控肥系统,这些都在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。
“现在国家鼓励乡村振兴、青年返乡,政府花很多心思在新农人培训上。”阿宽提到自己身边已经出现了“乡村CEO”“乡村运营师”等新职业,政府也会组织电商培训、职业经理人培训,让青年能在乡村找到自己的角色。在他看来,这些制度创新让浙江成为“新农业的前沿实验区”。而对他个人来说,“自媒体可能是最有用的技术,一定要做”。
让子弹飞得久一点儿
阿宽把农业看作是一场“长期游戏”。他清楚,这个行业的节奏缓慢,风险常在。“要让子弹不断往前飞,现在农产品越来越卷,电商也卷,价格也卷。质量提升不是短期的事,我做的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。”
他坦言,农业最难的部分仍然在于“靠天吃饭”。天气的不稳定,对植物是致命的,“几度的温差或者连续的阴雨就会给作物带来伤害”。经验和科技都重要,而科技的创新和运用,需要各行各业年轻人的持续投入。
今年7月,他在杭州钱塘重新组队,“我租的地本身是很空的一个地方,我们的加入瞬间让这地方多出来十来个人,就是感觉很‘嘈杂’!”他笑着说。每天虽然忙碌,却觉得踏实。“我感觉我天生就该干这件事。以前飞航班时挺迷茫,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。现在我知道我要做农业,我所有的努力,都是为了把它干好。”
阿宽现在和田园类模拟经营游戏挺像的,大致就是不断地组队、闯关、造东西、挣金币、买装备。未来三年,阿宽希望农场能自我运转,让团队里的年轻人都能靠土地生存。等到系统成熟,他想把经验带回东北老家,“那是更长期的一项事业”。







六年三次转身
许多的家在山东潍坊,父母原本是农民,但早早就进城打拼,成为家庭的第一代“城市人”。父亲开过超市,后来做外汇;母亲一直从事保险工作。受家庭影响,许多大学选择了金融专业。毕业后,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留在城市,而是决定走向田地。
“我当时进入农村,就是因为挣钱。”2020年大四,还没毕业就已经做过淘宝店、滑板培训,以及跟师傅学习种地,但疫情让一切归零,他开始思考下一步。偶然发现寿光的大棚种植收入非常可观,于是决定试一试。那年3月,还没毕业的许多跟着师傅学习种地,购买了人生第一个300米大棚,第一年种就卖了14万斤,纯利了20多万。到2022年上半年,他换了2个更宽的大棚,土地总面积翻了一倍。
许多的第二次转身出现在2022年9月26日。那时他开始拍短视频,“当时就是想拍拍短视频,试试带货,结果一发不可收。”其间一个叫“奶油黄瓜”的品类,做到了20000000的营业额,但他最后没有选择走直播带货路线,直到现在,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线下农业;而他的抖音账号,主要用来记录真实的农业故事与创业心路。
今年4月,他离开寿光,先后去了北京、雄安、衢州、云南等地寻找新机遇,最后落脚杭州。寿光作为中国的菜篮子,发展大棚种植和种苗行业有基础和优势,但消费能力和三产融合后劲不足;相比之下,杭州具备发展“农文旅”的城市条件,综合考虑后,许多开始了“采摘+咖啡馆+露营地”的“城市农业”探索。切身感受到种植、销售、三产融合等各条的农业赛道都越来越卷,最近杭州的业态逐步稳定下来,他又回到了寿光。这次要做的,是建立一个难以被轻易复制的农业平台。
Be Real:田园无牧歌
“很多人说自己喜欢种地,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伪概念。准确来说,这种喜欢是小规模种一些体验感强的作物;如果把种地当作主要经济来源,你就不开心了。就像把爱好当成营生,大部分人都不会开心。”许多从不相信有“美好的乡村生活”。在他看来,乡村并不是乌托邦。“如果乡村真的那么美好,就不会存在城市了。大家之所以都往城里跑,就是因为城市生活确实更便利。”或许有人将“回家种地”当作自己工作重压下的精神寄托,但是许多看来,成为新农人要面临的最大困难,就是“乡村容不下他们的肉身”。所谓的身体吃点苦,比如冬天顶风卖菜、夏天高温耕作,在许多看来并不算真正的困难;突然失去丰富的娱乐场所、唾手可得的美食外卖、方便的交通基础设施,只剩下眼前“贫瘠”的土地,是否还能重新耐受孤独,才是这道必答题真正的题面。
身体的考验之外,新农人还要克服心里对于未来的迷茫,许多感觉这一关甚至更难过一些。对于传统农民来说,烦恼或许源于“种出来的菜卖不上高价”;而对于刚刚入行,还没有获得正反馈的年轻人来说,“一城一池的得失”尚可接受,长期看不到务实的方向,才是他们难以坚持种地的根本原因。
许多乡村创业这么多年,他眼里的乡村的确是“美好的”,但这种美好来自他发现并抓住的机会本身。“我不在意有没有健身房、美女、电影院,我看中的是这里的机会。”他记得自己刚到村里时,还是个留着脏辫的滑板男孩,“村里人都觉得这个小孩不靠谱,怎么可能种地?”后来他种成了,又被劝“别乱搞短视频,做不起来的”。农村里的观念普遍对年轻人“不那么信任”,如果周围大多是怀疑的声音和目光,新农人必须自己先赋予自己绝对的信念。
金融思维,算法种地
“金融思维比技术更重要。”这是许多总结出的经验。他拿着父亲给的64万去建大棚,乍一听冒险,但他在投入之前就已经算清了这笔账:“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亏一年租金和种子,本金我可以一分不少地带回来。这就是同样种地人和种地人的区别。”
新农业的本质是创业,同样也是商业逻辑下的一种实践。金融学的系统学习经历,让许多最先关注各阶段战略的选择:“金融思维告诉我什么时候该种地、什么时候该拍短视频、什么时候从寿光走出来、什么时候再回去。”他把每一次扩张、转型、切换,都看成一次“投资决策”。很多时候具有前瞻性的选择,创造出的价值远大于盲目努力的结果。
比如他当年决心启动短视频,是在 2022 年夏天,大棚里连续干活十几小时,晚上村口超市买速冻水饺,3年来他第一次被问道:“许多,你打算挣多少钱走?”那一刻他意识到,如果种10年地挣二三百万离开,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也只会停留在“能干、吃苦”这一层。最年轻的10年,许多觉得可以给村子和自己创造更多:用短视频,把种地经验转化成数字经济,直奔“商业 IP”去做农业平台。
“阳光玫瑰葡萄现在种的人太多,已经烂市了;但消费者其实并不关注细分品种。科技水平提升让复制更容易,种菜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。”在他
看来,新农业真正的区别不在设备,而在思维。无人机、自动打药机大家都能想到去用,关键在于如何挖掘农业里可持续的商业价值——新农业的底层逻辑是算法,是模式,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和设备。
在汗水和泥土中干实事
“要从做农业的发心上去讲的话,我是一个商人;如果从我这六年做的事情来讲,我是一个农人。”在许多身上,农与商的身份并不冲突。2023年春天的一场“苗灾”成为他决定搭建种苗平台的起点。那年他栽了27000株苗,死了4000株。“我找苗场赔付,他们一看是我,怕我在网上曝光,马上说不用看苗,直接给我发新的。我连怎么和他们PK都想好了,结果维权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”这件事也让他意识到,如果是普通农民买到坏苗,他们没有影响力,所以根本没有维权渠道。于是许多开始思考:要怎么让所有农民都能买到真的、好的苗子?所有农民绕不开种苗,这必然的需求就是做平台的根本支点。
“签协议没用,商人是逐利的。我要让卖真苗的人赚到更多的钱,让卖假苗的死得干干净净。”从这念头开始,他启动了种苗平台计划。这个平台的逻辑是让农民直接交易,让优质商家能被看见,让坏商人无处藏身。他形容自己的定位:“我不当简单的种苗贩子,我要的是通过商业模式净化市场,用良币驱逐劣币。”他清楚这条路的艰难。“白手起家,爹妈是普通人,没有靠山。凭自己攒下来的人脉资源,已经拼了半条命。”但他依然选择在困难模式中向前。“人做事情无非三种:当官、出名、挣钱。我不想当官,也拿到过该有的名,现在就该挣钱。”不过他强调,“挣钱不是烂钱。只要还叫‘新农人许多’,我挣的钱就必须是有意义的钱。”
一路上崩溃不少,但许多从没真正放弃过。“农业本来就没有退路,你不可能说扔就扔掉自己的果子,不可能放下大棚。你像养孩子一样,从翻地、栽苗、浇水、打药、坐果期一点点看着它长大。只要果子没死,没有人会停下。”
和土地血脉相连
“我对新农人的定义,就是能让更多农业人更简单、高效地赚到良心钱。你只要能为产业带来价值,带来新质生产力,你就是新农人。”许多一直信奉这一点。任何创业都有风险,但是他相信依靠土地可以致富,“年轻人不一定要回乡种地,但一定要去发展农业。现在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问题,是没有靠谱、能干的年轻人。农业是年轻人的蓝海,但大多数人沉不下心。”
在许多的路径中,从2020年的大棚,到2022年的短视频,再到如今的种苗平台,他始终在不断的尝试与调整中,打造属于他的商业闭环。“我不聪明,所以我要选一个让我在里面是最聪明的人的赛道。我是主动选择进入农业,不是被农业选择了我。”他希望未来能把平台做到具备上市的条件,构建一个真正有商业潜力的体系。他的目标就是“今天要是有投资人站在我面前,我能讲出让他想投的理由”。
土地对于中国人来说,其所孕育的,从来不只是一棵作物,一类产业,还有一种血脉般的隐蔽延续。父辈从田地里走出去,子孙再带着从城市获得的知识、逻辑与视野回到这里。从乡土迈向城市,再从城市回望乡土,土地的力量一直在那里,它撑起中国人的饮食之根,也塑造了世代不断的韧性。
年轻人以新的方式耕耘,把数字经济、组织创新、品牌思维、供应链能力等现代模式,重新注入农业的躯干。许多眼前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,未来会继续生长出新的产品、新的职业、新的模式。而他的足迹,早已结实地踩进下一个即将抵达的未来。





在山林深处,李大胖与汤小果以一种近乎“21世纪隐士”的方式生活着。没有城市的喧嚣,也没有社交媒体上的虚张声势,他们的日子由天气、山路、植物与季节决定。一个是从小与草木为伴的植物爱好者,一个是看见重庆山火后决心“为森林做点事”的园林设计师;两个人在大山里相遇、磨合、并肩同行。

21世纪“隐士山人”
李大胖与汤小果通常在下午5:30下班,夏天晚一些,冬天稍早一些。回家后,他们会处理文书工作或制作标本。尽管林业技术员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工作,但方案撰写、调研设计、资料归档仍是日常必需。他们目前的工作,主要围绕松材线虫病的调查与治理展开。
汤小果 2022 年毕业后,曾在深圳做园林设计。她刷到重庆山火后,“觉得植物被烧掉很可惜”,便辞职来到万州,从城市园林走向真正的森林,也因此走进了李大胖的生活。大胖从小喜欢植物,高中时家里养了600多株花草,以至于“周围人觉得我有点变态”。他会把路边的花捡回家养起来,也会送花给老师和同学,有时也拿出去卖。毕业后他直接选择了林业,因为喜欢植物,也不太擅长和人交往,如今已经7年。“每天和花花草草、大山河流打交道,感觉不那么压抑,就很快乐。”
这些年,他们跟着项目走遍重庆37个区县,认识当地八九成的植物,但依然能不断遇到没见过的新物种。“很多地方都还在新发现物种,这个也很正常。”他们的排班依天气而定:晴天在山里尽量完成调查;下雨就在家写报告、做方案。寒暑不忙时,他们会把攒下来的调休拼成小假期,“我们工作是在这边爬山,休假还去爬山!连续几年去了川西、青甘大环线。”
这份职业的节奏与城市打工不同。它简单、自由、人际关系清晰,最累的是体力和山路。最多时他们一天走40000步、20多公里,往返爬升四五百米,山里无路可走,就靠经验、方向和对地形的熟悉。偶尔运气好,有村民能载他们下山,但多数情况下,他们总是自己探出一条新路。“山林环境可能比荒野求生节目里恶劣十倍。他们那种有路,我们走的是野山。”“松树钻蛀类害虫系统调查”,多采用对角线采样法,调查每天走不同的路线,他们工作场地多为喀斯特地貌,茂密植物下可能就是几十米深的暗坑。探路时,大胖总走在小果的前面。
“天上掉下来”的妹妹
在汤小果来到这里之前,大胖已经带过许多新人。但大多数人坚持几个月就离开,让他多次经历“认识、离开、再也见不到”的循环。“好不容易培养出来感情,加了微信,刚成为朋友对方就离开了,心里空落落的。”那之后,他不愿再投入过多的期待,对后来者都保持距离。就在他习惯封闭自己的时候,小果来了。
从小果的视角,大胖刚开始不理她,嫌她不懂植物,还质疑她守护森林的决心。她便憋着劲学习,见到不认识的植物就查资料、做笔记,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,最终留下来。“她为什么叫汤小果,就是因为她喜欢摘山上的野果、野蘑菇,‘小果’是我给她取的外号。”两人在山上采野果、野葱、折耳根,发现新植物,确认不是保护植物,就带回家做标本;漂亮的果子就被烘干收藏做摆件。季节更替、植物变化,都让日子从不缺乏新鲜感。“今天我们还做了几个野棉花标本,它在我们这种海拔低的地方很少见。”
他们也一起经历了山里的危险。有一次,大胖在林中踢到非法捕兽夹,被夹子绑在树上的钢丝绊倒后,大腿插到盗猎者削尖的竹子,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口。小汤背不动他,就和他一步一步挪下山。山里的危险还有马蜂、毒蛇、野猪,甚至前几天看到与五步蛇同科的腹蛇。家里人一直比较支持他们的选择,但是遇到蛇的事,两人没敢给家里面说。生活的艰苦,也容易让人萌生退出的想法。去年的一次车祸让两人受了重伤,大胖曾认真考虑过离开。但随着自媒体科普带来新的影响,他又重新坚定了7年前的选择:“每个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,有些事总需要人去做。”
从植物爱好者到林业工作者
尽管他们常驻山林,但生活并不“原始”。他们会跟着项目就近租房,若靠近城市,会优先选择住城里,因为购买设备、交通和整理资料都更方便。“不要把我们林业人想得太原始。进城买东西、逛街,跟大家没什么区别。”
他们目前的核心工作是治理松材线虫病。该病1982年首次在南京中山陵被发现,40多年来蔓延至全国大部分松林。至今没有有效根治方法,传播途径包括松墨天牛和人为携带。“评论区很多人都不知道松树有这种病。”治理流程从每年8月底的普查开始,需要统计死亡松树的数量与位置,并撰写报告、设计方案,随后提交专家评审。入冬后保持日常监测;病死松树要么集中粉碎,统一焚烧,要么在专业人员看守下就地处理。整个流程通常持续到次年3月底,4-7月查漏补缺,8月将开始新一轮调查。
此外,林业技术员的工作方还有古树名木复壮、林业资源调查、入侵生物调查,以及打药、修枝、松土、施肥、设置护栏等具体实施工作。不同地域、海拔、不同地貌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态问题,需要现场判断与经验积累。
行业里年轻人不多,很多林业大学的毕业生,也并没有选择从事森林保护的工作。大多数入这一行的人,最初就是单纯喜欢植物。从事林业不会让人大富大贵,刚入行薪资普遍不会太高;但是随着时间经验知识的积累,把事情做好,工资也会上涨;另外可以自学考取职称,收入会随之增加。大胖目前拥有中级职称,即使未来不做一线森林工作,也具备跨方向就业的能力。“很多网友担心我养不活自己,但我现在靠自己的积蓄在重庆买了车和小房子。”
无人机与 AI 技术突飞猛进,但目前仍然难以替代一线工作人员。无人机可以从高空识别树木表面状况,却无法判断内部病变,也无法识别信息库之外的新物种;山里地形复杂,信号不稳定,机器容易坠落且难以找回;面对地面塌陷、山顶落石、植被变化,机器人难以像人一样随机应变。未来一段时间内,林业仍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员。
有些人一直在意一棵树的死活
大胖参与过三次救火,每一次都成功扑灭山火并平安归来。第二次救火时因吸入灰尘,一个月咳嗽并伴有灰色痰,他却仍感到自豪。那次他没有让小汤上山,“她一直想上去,但她是女孩子,留着头发,确实很危险”。小汤在山下拍的视频没有过多剪辑后期,发到网上后,获得了很大关注,因为真实的故事已经足够打动人。事后大胖婉拒了大量媒体提出的转发表扬,“山火是乡亲们一起扑灭的,我不能一个人享受荣光;而且那时候重庆山火灭火过程中,有很多更值得报道的消防英雄。何况关注是把双刃剑,我也不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。”
有很多网红拍过他们的故事,视频流量都很好。他们自己的账号相比之下,显得数据平平。也有媒体拍了他们的视频去参赛,还获得了各种记者领域的大奖。对此他们并没有觉得心里不平衡。“我们做自媒体就是为了科普。只要有一个人看了我们的内容,不把染病的松枝带下山,其他地方就会少死一棵树,这就够了。”他曾拍的山林日常视频被多家媒体采用,当时全网相关词条播放量五六亿。其保护森林的理念,通过多次在央视的发声,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家乡人刷到视频,会拿着截图问他们在做什么,这些反馈都成为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在镜头里,他们素面朝天。有人惋惜他们没有在转瞬即逝的青春里装扮,但对他们来说,已经找到了另一片更让自己自由、满足的田地。“我们也不是野人,出去玩的时候也会打扮的。”进入行业时,大胖只有130多斤,现在胖了不少,“主要是中午吃得随便,晚上回来就一个劲补。”他的愿望之一是瘦下来,也希望“松材线虫病的发生面积能下降一半”。
李大胖与汤小果的20多岁,没有宏大叙事,却有更长久的力量——一种来自土地、来自植物、来自“不让一棵树白白死去”的执念。山林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节奏,也让认识他们的人重新理解“职业”、“成长”与“留下”这些词的重量。森林给了他们职业、伤疤、伙伴、爱情,也给了他们人生的方向。有人关心宇宙中永恒的真理,也有人一直在意山顶那棵松树的死活。





编辑 = 刘海伦 + 耿磊
摄影 = 马征
造型 = 李骁
撰文 = 沚蘩
灯光助理 + 摄像 = 杨明志(完美绽放)
妆发 = 魏再 + 余爽
妆发助理 = 黄超
新媒体编辑 = 霁阳
助理 = 静萱
排版设计 = 傅炯桦
热文回眸
是的,你们的男人装又回来了
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!
分享到朋友圈才是正义之举......
把我们加个“星标”
就能确保看到我们的推送
⬇️方法如下⬇️
富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